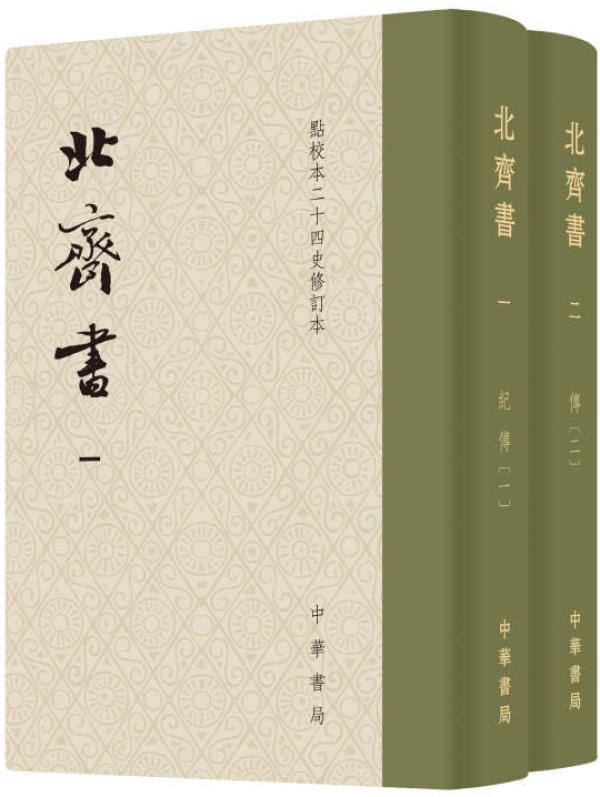
陈寅恪先生在其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写道:“北魏晚年六镇之乱,乃塞上鲜卑族对于魏孝文帝所代表拓跋氏历代汉化政策之一大反动”,“高欢、宇文泰俱承此反对汉化保存鲜卑国粹之大潮流而兴起之枭杰也”。陈先生仅三言两语便点明了北朝后期历史之转向。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胡化-汉化”问题呢?如果把“胡化-汉化”限定于统治人群之升降上,那么这样的看法并无不妥,而且颇具解释力。但如果把“胡化-汉化”简化为胡汉冲突,并以此冲突作为北朝后期历史的基本线索的话,那么这样的历史解释与历史真相之间便难免方凿圆枘了。
缪钺先生在他那篇发表于1949年的著名论文里提出,东魏北齐历史上先后发生了三次汉人与鲜卑人的政治冲突,皆以汉人失败而告终。此后,把胡汉冲突作为北齐政治史的基本线索便成了学界主流看法。当然也不乏批评与反思。例如,黄永年先生就曾指出,这三次政争与其说是胡汉民族冲突,不如说是个人权力之争。本文的主人公杨愔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杨愔是所谓的第二次胡汉冲突中汉人一方之代表,死于乾明元年(560)政变。可是,有一处细节却令传统的胡汉冲突论颇难以解释,那便是——研究者眼中以“鲜卑”自居、专事打击汉人的北齐皇帝高洋,为何会在临终前将辅政大权交给汉人杨愔呢?显然,单纯地以胡汉民族身份作为划分政治阵营之标准、以胡汉冲突作为政局演变之线索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本文的初衷并非检讨“胡化-汉化”视角之得失,而是试图通过对杨愔的个体生命遭际做深度解析,由此展示魏齐鼎易变局之下士大夫群体的复杂处境。
杨愔(511-560),字遵彦。关于他的家世,《魏书》作“自云恒(弘)农华阴人也”。“自云”二字道破了杨愔家族不过是“冒牌货”的真相。杨愔家族崛起于北魏孝文帝朝,自太和十九年(495)“定姓族”起,便由朝廷确立为弘农杨氏之正支。在随后的宣武帝朝,杨愔家族尽管在政治上遭到打压,但受惠于汉族高门“回归故里”之政策,杨愔的伯父杨播、父亲杨津先后担任本州华州的刺史,为其家族在乡里之经营保驾护航。杨愔出生于公元511年。四年后,随着宣武帝的离世,杨愔家族重返政治舞台的中央,家族的主要成员自华阴迁至首都洛阳居住。《魏书》所记载的那一番兄弟和睦、子孙孝顺的景象,便发生在洛阳之“京宅”。“京宅”中还设有学馆,杨愔少年时,“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杨愔家族本不以家学著称,学馆当是延请名师来教授。
发生于公元528年的河阴之变,给北魏统治集团以沉重一击。杨愔家族也自此步入了命途多舛的时期。不过请注意,杨愔家族并无一人死于河阴之变。这说明他们事先便被告知,不要前去迎接新皇帝。大概就像尔朱荣叮嘱元顺那样:“但在(尚书)省,不须来。”此时杨愔并不在凶险的洛阳,而在更为凶险的河北。孝昌元年(525),杨愔随父亲杨津赴任定州。紧接着,河北爆发了大规模叛乱,叛乱的中心正在定州。此后,杨津困守州城,三年后城陷,父子被执。叛军首领葛荣想把女儿嫁给杨愔,又逼迫他出任伪职。杨愔只好装病,偷偷口含牛血,再当众吐出,这才作罢。数月后,叛军被讨平,杨津父子终于获救。
回到洛阳后,杨愔仍旧称病,与好友邢邵隐居于嵩山。史书说他“以世故未夷,志在潜退”。杨愔的堂兄杨侃深得孝庄帝信任,参与了诛杀权臣尔朱荣的密谋。永安三年(530)九月,孝庄帝诱杀尔朱荣,旋即以杨津为北道大行台、并州刺史,命他直取尔朱氏的大本营晋阳。十二月甲辰(三日),尔朱氏联军攻破洛阳,俘虏了孝庄帝,杨津的军队也随之溃散。这次溃散中,杨愔与父亲杨津失散,讵料竟成永别。杨愔被抓后,在押送洛阳的路上,居然说动了押送的军官跟他一同逃亡。可是,天大地大又何处容身呢?杨愔去投奔了勃海高乾兄弟。他自然不会想到,这样一个求生的举动,日后竟会给自己的家族招致灭顶之灾。
勃海高乾兄弟是河北首屈一指的汉人豪强,而且是孝庄帝的支持者。孝庄帝诛杀尔朱荣后,高乾兄弟在乡里举兵响应。待到洛阳陷落,庄帝被执,高乾兄弟也随之偃旗息鼓。公元531年二月,尔朱兆遣人来,假称征发马匹,其实是要捉拿高乾兄弟。高乾兄弟为求自保而再度举兵,推举同郡士大夫封隆之为义军首领。这是杨愔投奔高乾兄弟之背景。与此同时,尔朱氏任命的幽州刺史刘灵助也在范阳豪强卢文伟的策动下起兵。一时间,幽、冀、瀛、沧四州(今河北省北部、东部)的汉人豪强纷纷响应。三月丙申(二十六日),刘灵助兵败身死,河北地区的反抗尔朱氏运动转入低潮。约在531年四月上旬(《北齐书》故意记成二月),尔朱兆的部将高欢“军次信都,高乾、封隆之开门以待”。那么,勃海高、封又为何会接纳高欢并奉之以为主呢?首先,高欢“扬声来讨”,对汉人豪强来说,不接纳之则首当其冲,接纳之则可托庇于高欢头上的尔朱氏大旗,由此得以保全。其次,汉人豪强此前便已派代表与高欢接洽,双方在反对尔朱氏的立场上达成了一致。
高欢初至信都,杨愔“投刺辕门,便蒙引见”。六月庚申(二十二日),高欢命汉人豪强高乾、李元忠袭取殷州,随后上表朝廷,正式与尔朱氏决裂。高欢举义后,“文檄教令,皆自(杨)愔及崔㥄出”。高欢义军的主体是六镇武人与河北汉人豪强,今得出自第一流高门的士大夫崔㥄、杨愔点缀其间,不仅壮大了义军的声势,而且扩大了其社会基础。可是,杨愔的家人还在尔朱氏控制下的洛阳和华阴。在尔朱氏眼中,杨家本就是孝庄帝的支持者,现如今又有人公然参与叛乱。于是,531年六月底及七月初,尔朱氏分别对居住在华阴和洛阳的杨氏家族成员展开杀戮。史载:“东西两家,无少长皆遇祸,籍其家。”
杨家的“家祸”乃是杨愔招致的,这在时间上若合符契。可是史书却极力淡化这一点,以至于今天的研究者往往受此误导,认为“家祸”的肇因是杨侃参与了诛杀尔朱荣之密谋。据墓志,杨侃于是年六月二十八日遇害于长安。果真要追究杨侃的话,又怎会等到六月底呢?《魏书·杨侃传》:“普泰初,(尔朱)天光在关西,遣侃子妇父韦义远招慰之,立盟许恕其罪。侃从兄昱恐为家祸,令侃出应,假其食言,不过一人身殁,冀全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为天光所害。”初看这段话,似乎是尔朱天光诱骗杨侃而杀之。实则恰恰相反,尔朱天光并未食言,不但“恕其罪”,更没有株连他的家人。《北齐书·杨愔传》载,杨愔初见高欢,便“陈诉家祸,言辞哀壮,涕泗横集,神武(即高欢)为之改容”。可是,此时“家祸”尚未降临,杨愔又如何“陈诉”呢?显然,《魏书》和《北齐书》皆为杨愔隐讳。
高欢推翻了尔朱氏专政,由此奠定了高齐王朝之基业。杨愔与高欢之间却似有隔阂,以至于杨愔曾一度化名避居。后来,高欢召回杨愔,除受官职,妻以庶女。但杨愔真正得到重用,则是在高欢的长子高澄居邺城辅政之后。东魏北齐采用两都制,政府的主体在邺城,军队的主力则在晋阳。高欢居于晋阳统兵,需要有人在邺城执政,高澄正是极佳的人选。高澄于兴和(539-542)初年入朝辅政,旋即任命杨愔为吏部郎,并大力拔擢士大夫人物。武定五年(547),高欢病逝,高澄接掌大权。不久,杨愔由吏部郎“超拜”为吏部尚书。两年后,高澄遇刺身亡,由他的次弟高洋嗣位。这次暗杀的内情扑朔迷离,行凶之人是一个名叫兰京的厨子。幕后的真凶又是谁呢?从种种迹象看,高洋的嫌疑最大。暗杀发生时,高澄正在与杨愔等少数亲信密谋改朝换代后的人事安排。杨愔“狼狈走出”,这才逃得一条性命。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高澄的亲信班子大体上被高洋沿用,杨愔也成了其中最受倚重之人。倚重到何种程度呢?且看时人之议论。颜之推《颜氏家训》云:“齐文宣帝即位数年,便沈湎纵恣,略无纲纪;尚能委政尚书令杨遵彦(杨愔),内外清谧,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无异议,终天保之朝。”卢思道《北齐兴亡论》云:“(高洋)爰及中年,诞纵昏德”,“赖有尚书令弘农杨遵彦”,“有齐建国,便预经纶,军国政事,一人而已”,“凡有善政,皆遵彦之为,是以主昏于上,国治于下”。《隋书·刑法志》亦云:“然帝(即高洋)犹委政辅臣杨遵彦,弥缝其阙,故时议者窃云,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对此需做两个层面的分析。一是事实层面,即颜之推、卢思道等人的看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二是书写层面,如若与史实不符,那么为何会产生“国治”“政清”之说。先看事实层面。若说高洋晚年委政于杨愔,尽管不够确切,但大致是成立的。至于卢思道所云“军国政事,一人而已”,则只可能出现在废帝高殷时期,绝非高洋时期的真实写照。颜之推所说的,高洋委政于杨愔之后,“内外清谧,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无异议”,亦非实情。《北齐书》云:高洋晚年,“自皇太后诸王及内外勋旧,愁惧危悚,计无所出”;甚至高洋死后,除杨愔外,“百僚莫有下泪”。显然,统治集团的上层绝非“各得其所”、各安其位。至于“政清”“国治”之说,宋人晁说之、叶适、元人李治都认为是溢美之词。
再看书写层面。颜、卢等人对杨愔所发挥作用的夸大,以及对高洋时期政治的美化,反映了士大夫对黄金时代的留恋。乾明政变后,顾命大臣杨愔被杀,勋贵势力抬头,士大夫群体则趋于消沉。直到后主朝,士大夫才再度活跃起来。后主慷慨地为杨愔等人平反,以此作为笼络士大夫的手段。随着以祖珽为代表的士大夫革新政治的努力归于失败,不久北齐王朝也走到了终点。士大夫在反思北齐亡国原因时,竟将症结归因于杨愔之被杀。颜之推云:“遵彦后为孝昭(高演)所戮,刑政于是衰矣。”卢思道云:杨愔被杀,“君子是以知齐祚之不昌也”。
“昏主”高洋与士大夫究竟是怎样的关系?高洋重用士大夫,是比较容易解释的。无论是从压制勋贵、伸张皇权的角度,还是从确立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政治的角度,高洋都必须重用士大夫。值得追问的是,高洋在士大夫之中为何会选中杨愔?除了杨愔本人所具备的门第、才干因素外,是否还有深层的背景呢?
其实,高洋重用的士大夫人物不止杨愔,还有高德正和“三崔”(崔暹、崔季舒、崔昂)。四人先后官至尚书仆射,与杨愔共同执政,却又是杨愔的政敌。杨愔何以能在与高、崔一派的竞争中胜出呢?我们认为,杨愔获胜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他是士大夫中主流派别的代表人物。这个主流派别,正是北魏洛阳时代士大夫的“核心”人群,不但门第崇高,人物众多,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标榜正朔所在,他们都是重要的人才资源。日后,也正是他们(及其子孙)掌握着历史书写的权力,把杨愔推上了神坛。
在天保后期,高洋还有一块“心病”,这便是太子接班的问题。高洋生前,对太子的嗣君地位构成挑战的是高洋同母弟中年龄居长的高演。早在魏齐禅代之际,高洋命人为太子起名,当他得知“名殷字正道”后,便感慨道:“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后儿不得也。”又对弟弟高演说:“夺时但夺,慎勿杀也。”可以说,对皇位传承的焦虑,始终贯穿了高洋天保(550-559)一朝。
高洋屡次三番设计除掉高演,但最终不能得逞,主要是由于母亲娄太后的庇护。传位高演,他不甘心,改立次子,亦无成算,那么他所能做的,就只有在身后的人事布局上做文章了。杨愔正是高洋选中的首席顾命大臣。以“鲜卑”自居的高洋之所以要向汉人杨愔托孤,还有一层重要考虑,即娄太后是勋贵势力的首领,又是高洋传位于子的首要障碍。因此,高洋排除掉宗室、勋贵,而将少主托付与士大夫。
天保十年(559)十月,高洋死,太子高殷继位,次年改元乾明。值得注意的是,高洋卒于晋阳,高殷于晋阳即位,可是政变却发生在邺城。乾明元年(560)正月,高殷一行自晋阳还至邺城。这应当出自杨愔等人的推动。政变后,高演对王晞说:“不早用卿言,使群小弄权,几至倾覆。”这里的“群小”便是指杨愔辈,“卿言”则是指王晞曾建议高演在晋阳先发制人。可知,只要朝廷在晋阳,娄太后与高演一方便握有优势。这或许与他们对军队的影响力有关。
就在政变前六天,二月己亥(十七日),朝廷公布了新的人事任命,以皇叔高演为太师、录尚书事,皇叔高湛为大司马、并省(晋阳)录尚书事。这项任命的真实意图是出高湛于外,将二王分而治之,至于高演,则难逃被架空的处境。乙巳(二十三日),高演、高湛兄弟假意接受任命,“于尚书省大会百僚”。这天一大早,高湛在尚书省埋伏了家僮数十人,随后在宴会上逮捕杨愔等人。得手后,“二叔率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拥(杨)愔等唐突入云龙门”。在殿上,娄太后中坐,少帝高殷及其母李太后侍立。“时庭中及两廊下卫士二千余人,皆被甲待诏。”这是高洋留给高殷的最后一张王牌。可是,由于杨愔等人先已被执,李太后和高殷失去了主心骨。娄太后先是歇斯底里地发泄了一通情绪,尔后又向李太后起誓,说高演“无异志,唯去逼而已”。就这样,在娄太后的威逼与哄骗之下,李太后和高殷放弃了抵抗。
乾明元年政变,以杨愔一党被清洗,朝政大权落入高演手中而收场。政变后,高演为大丞相,旋与娄太后赴晋阳。六个月后,高殷被废,高演于晋阳即位。正如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的那样,乾明政变的实质是对最高权力的争夺,而非胡汉冲突。但政变后,勋贵势力抬头,士大夫群体趋于消沉,也是客观事实。有一则著名的例子。政变后,高演任大丞相,以心腹王晞为司马。“每夜载入,昼则不与语,以晞儒缓,恐不允武将之意。”高演对勋贵之曲意迁就,可见一斑。
尽管乾明政变给士大夫群体造成重创,但我们却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政变的发动者高演和娄太后对士大夫有所敌视。事实上,即使在相对恶劣的政治环境下,高演还是任用了一批士大夫人物。只不过,他不能再像高洋那样把行政大权交付给士大夫了,而是仅仅委以顾问应对、起草诏诰、教育太子等职责。不独高演如此,就连娄太后也并不敌视士大夫。乾明政变中,高演等人在外得手后闯宫上殿,娄太后“因问杨郎何在”,当得知“一目已出”后,“怆然”道:“杨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娄太后之所以称呼杨愔为“杨郎”,这是因为杨愔娶了娄太后的次女,也就是东魏孝静帝之高皇后。假若说这尚且能用家人之情来解释的话,那么娄太后接下来的举动就明显释放出了政治信号。“太皇太后临愔丧,哭曰:‘杨郎忠而获罪。’以御金为之一眼,亲内之,曰:‘以表我意。’”娄太后对落败身死的政治对手施以优礼,自然有安抚、笼络士大夫群体的用意。史又云:“常山王(高演)亦悔杀之。”可见,在处理士大夫问题上,娄太后和高演的态度是相近的。娄太后不仅不排斥士大夫文化,而且为其子高济娶一流高门清河崔㥄之妹,婚礼前还特别叮嘱道:“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给政变的双方贴上“胡”“汉”标签。
纵观北齐二十八年的历史,从魏齐禅代到乾明政变的十年是一个阶段,也就是高洋、高殷时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皇帝任用士大夫而抑制勋贵。在此阶段,北齐国家朝着建立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政治的轨道前进。这一进程最终被乾明政变打断。政变后的高演、高湛时期,士大夫群体长期受到压制,直到后主高纬即位后情况才有所改观。但好景不长,在后主朝激烈的政争中,士大夫遭受了更为沉重的打击。士大夫追忆杨愔、归美杨愔,我想绝不仅仅是出于对黄金时代的留恋,一定还有对他们所秉持的文化价值的坚守。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